10
來自黑暗大陸的良心
─納丁.戈迪默的「種族∕政治」文學
我飛的太遠了,我環顧四週,
只有孤單才是我唯一的伴侶
-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南非種族政治的解放、黑白種族隔離政策的廢除、黑人精神世界的風拂雨露、黑白關係的情愛糾葛,都無法離開納丁.戈迪默一生的作品與社會活動。她為南非那種階級上下、白肥黑瘦的「兩色社會」做出了極度寫實的藝術性描寫。寫實一詞在她筆下,意味著人們對殖民主義和種族政治不必存有過多的想像,只要睜眼凝視、伸手觸摸,一種「人壓迫人」的社會現實就會呈現在你的面前,進而在你的心裏放大、擴散和發酵。納丁.戈迪默不僅是非洲黑人忠誠的盟友,更是20世紀爭取人類良心復甦的勇敢戰士。1991年瑞典皇家學院以「在一個員警國家的審查制度下,勇敢而直接推進了告別種族歧視之歷史進程」為贊詞,授予這位白人女性作家諾貝爾大獎。儘管有人認為,在奈及利亞的索因卡(Wole Soyinka)和埃及的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之後才把獎項贈予戈迪默,瑞典皇家學院實在有點「遲鈍」。
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年出生於南非約翰尼斯堡一個礦區小鎮史普林斯(Springs)。父親是一位來自立陶宛(Latvita)的猶太裔珠寶商人,母親是英國後裔,幼年在天主教修女學校就讀,後進入威特沃特斯蘭大學(Witwaterstrand University)。儘管大學教育只讀了一年沒有取得學位,但戈迪默卻依賴自修自讀成為「小時了了」的作家。戈迪默9歲就能在家中寫作,13歲開始給當地的「星期快報」(Sunday
Express)撰稿,14歲就以題為《明日再來》(Come Again
Tomorrow)的短篇故事刊登於當地「論壇」(Forum)雜誌的兒童版上,年僅20歲就已是當地知名的專欄作家。28歲那年,美國「紐約克」(The New
Yorker)刊出了她之前所發表的作品,隨後美國知名期刊「維吉尼亞季刊」(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和「耶魯評論」(Yale
Review)也發表了她的作品。
由於具有一種「歷史預見」的能力,戈迪默的小說被譽為一種「預言現實主義」文學。她是一位真正多產的作家,計有15部長篇和200多部短篇小說,從1953年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虛妄年代》(The Lying
Days)以來,戈迪默的筆耕生涯從未中斷。她的作品多以南非社會的階級問題、家庭關係和黑白衝突為主題,從人道主義立場述說黑人革命解放的心理與行動。在此之前,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南非白人英語作家對戈迪默的創作生涯產生了重要的啟蒙作用,他就是任職教師和少年教養院院長的艾倫.佩頓(Alan Paton, 1903-1998),他在1948年出版了《哭泣吧!親愛的祖國》(Cry, The
Beloved Country)以及以種族歧視為題材的《太遲了,法拉羅普》(Too Late,
The Phalarope, 1953)兩部小說。《哭泣》通過一位祖魯族(Zulu)牧師庫馬洛(Stephen
Kumalo)和兒子阿巴沙龍(Absalom)的經驗和感受,描寫了南非各階層人民的生活,嚴厲指控白人把自己驕奢淫逸的生活建立在黑人生畜般的過度勞動之上。小說以黑白對比手法對土著區充滿屈辱與困苦生活的描述,對黑人深度的關懷與同情,給予戈迪默很大的衝擊,也間接塑造了戈迪默終生「留守故土、在地奮鬥」的寫作立場和主題意識。
自1642年荷蘭人(後來在南非稱為「布爾人」[Boer])占領南非開普敦以來,南非就陷入荷蘭人的非法占地和拓荒侵略之中,隨後經歷了英國與荷蘭人為爭奪南非控制權的慘烈鬥爭以及兩次的「英布戰爭」。1948年代表荷蘭極端種族主義的國民黨執政,開始推動反動至極的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僅占13%的白人統治著占了87%的黑人人口,貧苦的黑人被剝奪政治、教育、財產、婚姻等等的基本權利。戈迪默自幼就親眼目睹黑人礦工備受白人雇主的欺淩與壓迫,在文學創作上又受到種族議題小說的深刻鐫染,她以一種橫立在種族藩籬和愛情兩隔的位置,在一個充滿員警暴力和書檢制度的國家裏,通過「跨越凝視」的細緻觀察,為南非寫出一系列愛恨滄桑的「人民內史」。
戈迪默並不是一位反種族主義的宣傳家,也不是一位政治文學家,但她堅持要為種族政治作出獨立的藝術表述,以藝術再現的形式寫出種族政治對人類關係深刻的扭變和重壓。這種創作使命,使戈迪默全部作品具有高度同質性的主題,始終縈繞在自信與背叛、權力的談判、家庭的聯合與分裂、性別壓力、地理政治、家園觀念、種族、階級和女性情欲問題上。但這些議題無不圍繞在「種族隔離」這一核心制度,以及這種制度對人(無論是黑人或白人)的自我構成(ego-formation)和意識深層的異化性傷害。文學評論家安卓.伊丁(Andrew V. Ettin)指出,通過戈迪默的作品可以得知,「種族隔離」不僅對非白人形成深重的壓迫,也影響了人們之間關係的每一層面以及人們看待自己的概念,從南非外部來看,也許人們會以為種族隔離只是一種內含欺騙和權力濫用的系統結構,在私人領域中仍然可能維持誠實與信任,其實不然,種族隔離制度不僅是一種「變態」(anomaly),而且是一些廣佈在人們經驗與行為上一種明顯可見、公開宣示的態度與行動。種族隔離是一種態度與情感的預設結構,它像是一種用來區分之後再予歸類的標準,「統管」著包含分開、分類、禁鎖和宰製一系列的壓迫系統。
戈迪默漫長的寫作生涯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1953─1975年為第一階段,作品力圖在對應於種族政治的現實之外,建立一個具有藝術表達形式的種族批判文學;1976─1990年為第二階段,戈迪默傾向於創作歷史預言性質的政治敘事文本,表達出一種人道正義的信仰必將克服權力自私的革命想像;1990以後是戈迪默藝術風格抵達高峰的第三階段,一連串兩極化人生價值的搖擺式體悟,表達出不再計較「社會現實」而是回返「人性真實」的一種藝術返航之路。
戈迪默第一篇長篇小說《虛妄年代》描寫種族隔離下一場絕望無期的愛情悲劇。故事以一位白人女子賀倫(Helen)為主角,她愛上一位黑人青年,兩人純真的愛情後來在異族禁婚的壓迫下宣告破碎,故事表達了膚色之別對作為人類本質之愛的禁制。《陌生人的世界》(A World of Strangers, 1956)透過一位從英國來到南非工作的托比.胡德(Toby Hood)的親身觀察,展示了一個白人奢靡豪華、黑人窮困潦倒的「黑白世界」。兩個世界既是毗鄰而居,又是彼此孤絕陌生。對於南非這個黑白二分的國家,托比形容當他看完旅行手冊之後,感覺像是在遙遠的海外閱讀另一個國家,但實際印在手冊上的國家卻又像是不存在於星球上的另一國家,這個國家總是充滿了沾染螞蟻和惡臭的可樂瓶子,美麗的事物上總是沾著骯髒的手印。小說展現一種「雖然贏得友誼但膚色界限卻難以跨越」的社會情境。作為一個「外來的敘事者」,托比像個匆匆來去的過客,一個膚淺的白人中產階級,他沒有偏見也沒有正義感,他生活在南非卻形同外人,他眼見所有的不正義卻又完全接納它,一個白人自由主義者即使看盡殘酷的種族主義罪惡,依然可以裝出一副「不然你還期待什麼」的風涼態度。深層來看,戈迪默試圖通過對托比這一位角色既暗諷又期待的描寫,來區分「南非白人」和「白種非洲人」(white African)的不同並傾向於後者,通過重建一種新的社會自我意識和「白人本土化」過程,尋求一種超越傳統黑白對立的新國家認同。在某種意義上,這部小說不僅是新國家認同的探索,也是戈迪默本人重建自我認同的心路寫照。
《戀愛季節》(Occasion for Loving, 1963)寫的是一樁黑白糾結關係的不倫戀情及其悲劇下場。一個猷太學者博茲.戴維斯(Boaz Davis),熱情地周遊南非各地探尋非洲音樂,他的妻子安(Ann Davis)與一位黑人畫家吉登.席巴路(Gideon Shibalo)發生戀情。諷刺的是,博茲始終站在爭取自由的黑人這一邊,她的妻子卻縱情於玩弄兩個男人感情之間。小說在表現「情欲自由」與「種族藩籬」的兩難性,在嚴酷的種族法律下,小說人物終究無法以善果告終。
《資產階級世界的末日》(Late Bourgeois World, 1966)則是一部政治意味濃厚的小說,描寫一個善良白人因為無法與黑人犧手共處的心理障礙而走向自我毀滅的故事。戈迪默公開指責種族隔離政策對黑人與白人不分彼此的腐蝕作用,她公開鼓吹白人應該承認黑人的政治權利,甚至預言白人資產階級最後的出路就是認同黑人、與黑人合作。這部和《陌生人的世界》以及後來的《伯格的女兒》一起遭到白人政府嚴厲查禁的小說,以幾乎提早20年的時間,預見了後來白人政府的失勢和垮臺。
1971年戈迪默再度出版政治色彩更為濃厚的《尊貴之客》(A Guest of Honour),描寫一個新獨立黑人國家尚比亞(Zambia)三個不同政治人物的故事,在這部小說中,戈迪默似乎預言了對一種「黑人民族主義」的疑慮,為後來的黑人獨裁作出了藝術性警示。
《生態保護者》(The Conservationist, 1974)描寫一位白人富商梅林(Mehring)坐擁重金購得豪華莊園,完全無視於外界的苦難而過著特權式的孤立生活。戈迪默塑造了這位「世界只為我服務」的白人自私主義人物,他也許看到了黑人的痛苦生活,但是他無動於衷、麻木不仁,從不設法改變,甚至以種族和階級優越意識來區隔自己與外界窮人的界線,以身體和精神上的單身主義來滿足他的白人特權。在戈迪默筆下,人們看到了一個充滿偽善假惺、唯利是圖的白人世界觀以及她特有的現實主義藝術表現手法。這部小說獲得了該年度的布克獎。
1976年發表的《伯格的女兒》(Burger’s
Daughter)是戈迪默中期創作生涯的代表作。和先前兩部作品一樣,小說一發表就遭到南非政府的查禁和銷毀。查禁的理由是「女作家把小說主角羅莎(Rosa Burger)的故事當作導彈發射台,對南非共和國發射粉碎性的重量級攻擊」。小說出版後,南非政府一直軟性逼迫戈迪默離開南非,但她拒絕遠離,堅持選擇一種「在家流亡」的精神反抗方式,在自己的國家繼續寫作。
《伯格的女兒》是戈迪默為抗議1976年南非白人政府強迫黑人青年放棄本族母語,改學「布爾語─南非荷蘭語」而爆發「索偉托」(Soweto)屠殺事件而作的。羅莎是父親為紀念共產主義革命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而為她取名的。羅莎的雙親相繼因反對種族隔離政策而死於獄中。年僅18歲的羅莎利用探望獄中母親的機會傳遞革命訊息,「革命的恐懼」和「愛苗的滋長」陪伴羅莎渡過青春歲月。雙親死於獄中之後,羅莎流亡歐洲,但留亡在外的歲月依舊無法揮別雙親革命事蹟和祖國反種族鬥爭的記憶,她決心回國以她習得的醫療技術為「索偉托事件」受害者治病,但最終還是不敵白人政府的迫害而遭到監禁。在這部小說中,戈迪默輕描淡寫了反種族鬥爭的現實情況,改用一種心理分析的角度,通過羅莎心路歷程的自我探索和成長,探討一個生活在未出生前就已被命定的政治環境所支配的小女孩,如何經由記憶的反思和歷史的回溯,達到對自我意識和民族命運的最終體悟。戈迪默旨在表達一種「無人可以置身歷史之外」的革命意念,地理逃亡只會加重罪惡感對自己的嘲諷和腐蝕。小說也間接表達了戈迪默自己的信念,她把南非看成自己土生土長的祖國而不是「白種寄居」的殖民地,她絕不離開與之徹底絕裂之白人政府統治下的家園故土!
1981年的《朱利的子民》(July’s People)是戈迪默創作中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讀來令人感到歷歷如生、緊張萬分。這是一部歷史預言寫實小說,以過去式時態構逐了相對於寫作時刻處於未來可能發生的種族對抗事件。黑人武裝反抗即將取得勝利,白人的特權與統治地位即將失去,主奴關係(master-slave relation)即將顛倒互換。故事開始於一個白人家族在他的黑人僕役掩護下開始逃亡。
並非所有的白人都是種族主義者,故事主角巴姆.斯邁爾斯(Bam Smales)是一個同情黑人處境的進步主義者,儘管與妻子莫琳(Maureen)及其家族的政治態度截然不同,但巴姆始終相信並支持「黑人自治」的權利,15年來也一直善待家中奴僕朱利(July)。當種族戰爭漫延到巴姆一家所居住的約翰尼斯堡時,朱利建議主人跟隨他逃往偏遠的黑人部落避難。失去一切的巴姆一家不僅需要黑人部落的保護,也開始學習和尊重黑人的生活與習俗。然而,長期的種族隔閡與仇恨不是一日可以消解的,異族共處和相互依賴的困惑和掙扎,一直啃噬著人性本有的寬容和善良願望。於是始終認為種族隔離乃是天經地義的莫琳,不僅不能被黑人婦女所接納,而且決心逃離黑人部落,即使拋棄家庭也在所不惜。朱利的妻子與母親不歡迎巴姆家人到來,因為窮困的部落無法供養這個貴族家庭,朱利只好「霸佔」巴姆的吉普車以平衡黑白財富的不均。巴姆鼓勵黑人酋長們團結抵抗白人,沒想到族人卻以借用他的槍隻來打獵作為交易條件,酋長甚至試圖利用巴姆來對付其他黑人部落,以擴大自己的地盤,巴姆處於背叛白人的內咎和不再同情黑人的雙重絕望中。最後,故事結束於莫琳為逃離部落而奔向一部降落的軍機,消失在不知去向的命運中……。
《朱利的子民》並不是簡單地表達一種白人末日的武斷猜測,而是試圖展現並剖析處於動亂和急變狀態下更為複雜的種族關係。戈迪默運用了現代小說的技巧,通過流轉式的敘事角度,以「破折號」作為段落串聯的跳躍式寫作方法,使讀者在一種充滿閱讀張力的情境中,不斷追逐節奏快速的劇情,體會焦灼困惑的人性。
1987年的《大自然的運動》(Sport of
Nature),融合了革命愛情與政治熱情,描寫一位自幼被母親拋棄的白種猶太女子海麗拉(Hillela)勇敢投身黑人抗暴運動的故事。海麗拉是一位美麗又充滿智慧與精力的女子,她自絕於自身所屬的白人中產階級價值觀念,完全以黑種「革命之女」的角色自居,以致不為她的白人家族所容,只好離家前往當時革命流亡者雲集之地─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Dares Salaam),繼續與黑人革命事業為伍。海麗拉這一角色的塑造意味著和平解決南非種族問題的理想願望已告破滅,她先後與數名黑人運動領袖交往,幫助黑人領袖完成革命事業,最終推翻了南非白人政權,成為黑人國家的「國母」。
《大自然的運動》是一部黑人抗暴與起義的史詩小說,內容擴及整個非洲大陸,時間跨越1950─1980年代,虛構劇情與真實事件交叉並行,像是一聲黑人爭取主權獨立最後決戰的號角,記錄了黑人各種反種族隔離抗議運動,特別是南非白人政府一手導演的「沙佩維爾大屠殺」(Sharpeville massacre),描寫泛非洲人會議和泛非國民大會的鬥爭事件、曼德拉領導的地下革命運動等等。小說表達了戈迪默明顯的社會主義政治傾向,獨立後的黑人國家實施社會主義公有制度,南非從此脫離了白人殖民地的地位,成為全體非洲人共享的樂土。
儘管並沒有改變寫實、直述的敘事風格,戈迪默1990年以後的作品以更坦率又成熟的心理透視,通過人物內心的精神元素,包括欲望、意識、夢境、自覺、意志等等,來反映社會現實對人的命運的悲情捉弄。1990年的《我兒的故事》(My Son’s
Story)是戈迪默最成功的作品。
《我兒的故事》以一個反種族隔離的小學教師索尼(Sonny)一家四人─妻子艾拉(Aila)、兒子威爾(Will)、女兒貝比(Baby)─為背景,故事聚焦於索尼和一位白人女子漢娜(Hannah)因政治觀點相互契合而產生革命式的「地下戀情」。故事開始於威爾在一家戲院出口撞見並洞悉父親的婚外情,劇情展開於周遭承受婚變與家變雙重打擊下人物心理之「創傷─治療」的過程。表面看來,戈迪默似乎將「黑人正義」化身的索尼及其反種族隔離運動擺作幕後背景,集中於描寫陷入婚外畸戀和家庭破碎的漩渦,但正如劇情是映照在布幕中的人物故事,小說的重點毋寧是被戈迪默隱退在現實背後的種族主義精神壓迫,以及被「側面─反射」描述下黑人少年(女)的心路歷程,藉以突顯一個遭受愛情與社會雙重擠壓下黑人女性(民族)蛻變重生的形象。
索尼原是兒子威爾(Will)的英雄偶像,然而父親一場被窺知的婚外情使威爾跌落在絕望的谷底。作為小說第一人稱的敘事者,威爾不只是一個講述自家故事的小男生,他的敘事角色實際上是戈迪默「多重敘事策略」的再現者,在他身上承載了民族、家族、個人、意識等等情感與事件之多重線索的敘事網絡。威爾雖然在得知父親的婚外情之後對父親倍感憤怒,但因出身在革命家庭,血液中流的不只是父親的血統,還有革命意識的基因和符碼,個人心理的成長註定離不開民族意識的成長。貝比則是一個早熟的叛逆少女,具有孤僻式的革命熱情,她在自殺不成後離家,不是賭氣或逃避,而是把自己的身體和意志交付給父親早已為她塑造的民族事業。通過威利和貝比這兩位姊弟,戈迪默展示了一種藉由個人欲望流動來表達民族意識之深化與成長的敘事策略,將民族敘事和欲望敘事融合,並最終轉化為主控自己民族命運的超越力量。
索尼與漢娜的婚外情與其說是一種道德越軌的不倫之戀,不如說是一個黑人在政治壓迫下尋求情欲擴張以換取主體欲望之修補的精神異化過程。戈迪默把索因和漢娜的性愛比喻成革命運動,把他們的作愛描寫成「革命的交媾」。小說中不斷以意識流手法,探索由於長期處於隱秘和地下化的反種族政治行動中,一種隱蔽、暗藏、匿名的反抗式自戀,如何在索尼這一表面正直人物的潛意識中來回衝決和激盪。佔有一個白種女人一如顛覆一個白人政權,一種替代性的政治快感滿足在白種女人坦露的「獻體儀式」中。地下情欲一如政治主體欲望,前者因後者而膨漲,乃至決堤滅頂。地下暗房作為反抗者維繫尊嚴與安全的避難室,情欲泛流像是在暗道中仰望唯一透光的窗口,無論甘願終生監禁還是決心越獄重生,自由與尊嚴的最低消費都是一場生死未卜的犯難。
對於漢娜這個傳教士後裔、人權組織代表、黑人權益激進的擁護者,戈迪默並沒有給予她濫情化或神話式的拔高,也沒有給予庸俗的道德譴責,但對於她付出於索因的愛情以及對黑人解放事業的襄助與同情,戈迪默具有一種穿透性的解剖能力。在這個金髮碧眼女子的微笑背後,總是暗藏著「救助別人所表現出來既懷歉意又心滿意足的神情」,她似乎更願意以共享一夫而不是橫刀奪愛來展示她願意與黑人共用「平等」理念,乃至於實現自身作為「白人罪惡獻祭者」、「白人負擔的釋放者」這一角色。漢娜的縱欲意味著通過肉體獻身達到白人道德的滌淨,佔有意味著讓黑人從她的身體取得滿足,而後原諒白人的種族罪行。實際上,索尼對漢娜的魅力,從來就不是索因所從事那些令人敬畏的黑人進步事業,反而是索因作為一個黑種男子的「原始資質」,一種索因自認羞恥卻令漢娜為之神魂顛倒的黑性原味。
索因的妻子艾拉則是戈迪默刻意塑造的黑人女性角色。她原是個溫柔婉約的女子,但人們沒有看出她溫柔外表背後堅定的民族意志。她把全部心力奉獻在她偉大的丈夫和家庭,但並不意味她只能做個「閨房天使」或「廚室嬌娃」。在面臨種族壓迫和丈夫背叛的雙重打擊下,艾拉選擇了不是悲痛自憐的怨婦,而是為民族革命獻出餘生的堅強女性。她實現了丈夫沒有完成的理想和事業,通過選擇作一個民族女性而不是男性附庸,艾拉以自身的命運塑造了一個真正自覺的黑人女性典範。
1994年的《無人伴我》(None to accompany Me)是戈迪默所有作品中最具藝術風格與哲理內涵小說,不僅具有莎士比亞式古典浪漫的韻味,也兼具存在主義的生命省思和現代派的詩性氣息。小說發表時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已經崩潰,第一屆全國性民主選舉正在舉行,南非正處於步向「後種族隔離」(post-apartheid)的劇變時代。然而,小說並不在表現黑人解放後的激情與狂歡,而是聚焦於一個爭取黑人權益的白人中年女性律師維拉.史塔克(Vera Stark)60年生命歷史的反思,以及一個黑人家庭迪迪默斯(Didymus)因政治環境變化而與妻子西邦姬雅(Sibongile)反目對立的故事。和過去幾部小說的人物典型相似,戈迪默再度塑造了一種在外表上為公益獻身但內心卻纖細敏感、脆弱不堪的典型人物,小說描繪了劇烈的政治變化對人際關係和家庭倫理一種「時不我予」、「悔時已晚」的衝擊,表現出自我在情欲世界終究無法安身棲息的掙扎和痛楚,闡述了「孤獨」作為一種生命本質而無法揮除的黏著性與本真性。
維拉.史塔克是一位在新政府成立之後積極為黑人爭取土地和住房的優秀律師,一如過去熱情協助黑人運動,她還積極參與南非新憲法的制定。史塔克是一個政治活躍份子,堅持公平與正義的原則,但她同時也是一個內心空虛、情欲旺盛的放蕩女子。在丈夫外出時,她與英俊的黑人男子貝內特(Bennet)陷入情網,在難忘舊夫之下,腹中懷著舊夫之子與新夫貝內特結合。史塔克擁有與舊夫所生的兒子和與新夫所生的女兒,但女兒成為同性戀者,兒子亦終生陷於感情困局中。貝內特最後也因經商失敗而離開深愛的妻子,史塔克借住一位黑人朋友家,簡居在車庫改裝的破落小屋裏,獨自一人走完生命餘日,至死無人相伴。
謊言、自欺、投機,堅持正義又貪權癡欲,充滿在小說人物的生命歷程中,在種族偏見、政治鬥爭、信仰危機中,人們雖有長話交談、午夜纏綿,但沒有真正的溝通與信任。對此戈迪默不作價值判斷,也不虛擲同情,只是一絲絲、一層層剝露出社會歷史對人性的扭力和覆蓋,展示出人的「自我」在時過境遷中的變形乃至無法辨視。忠誠與背叛、奉獻與自私、佔有與喪失、寬容與忌恨,無不都是人性中多面並存的本質,它總會在情境與利害中不自覺的爆發。史塔克原來以為情欲之愛就是自我的交托和付出,到後來才知道,自我不是一張床,可以任意和擁被共眠者分享;生命是一場孤獨的行走,起站和終點都寫著「孤獨」同樣的站名。人無不都是一種被無端拋入於世的偶然性,微小而脆弱地伏游在不可知、不確定的人際變幻中。小說中,史塔克與一名黑人同事在路上遭遇搶劫,兩人中槍倒地,四處無援。此刻,孤獨與死亡的恐懼像是一塊巨大的黑幕緩緩落下,在浩瀚的天空下兩人像是一堆廢物,被丟置在一條空寂無人的泥路上,被拋棄在逐漸退色的景色裏。垂死中的他們,躺在月光反照的地面上,像是一棵斑點,很快就會在風吹雨淋下,消失縱影。
和過去的小說主題明確、文字簡要不同,《無人伴我》是一部藝術性很高的作品,戈迪默以其優雅醉人的文字表達了一個知性與情欲不能兩全的女子,在風殘燈盡後的感傷和體悟。整部作品,無論是借景繪心或是托心看景,將心境之孤寂幻化為蒼涼無盡的物景,或是以樹枯雨冷來況喻心路已盡、人生幾何的感觸,不僅是戈迪默晚年一種遲暮回春、千帆過盡之人生態度的寫照,也使這部作品登上美學高峰的境界。在一段描寫史塔克寒夜中悄然離去的場景,戈迪默以詩化的筆觸寫道:
維拉走了出來,一道刺骨的藍色冬日之氣迎面而來,像是跳水一般地
墜入美妙的震盪之中。……寒冷的空氣風乾了她的嘴唇和眼臉;樹林
中併排的木椅和桌子,佈滿層層晶瑩的冷霜。萬物脫去了外衣,在被
擦亮得光溜溜的樹枝上一片葉子也沒有。一叢叢灌木像糾纏成團的金
屬線,乾枯的棕櫚樹像她僵硬的手指。這時候,一串厚厚的碎冰把她
眼前的視線打亂,閃爍的星光令她眼花繚亂。她把頭輕輕縮回,在搖
擺顫動的星空下,她來回的走著,然後,繼續上路。她的呼吸像是一
幅舒展開來的捲畫,在她的面前留下……一個簽名。
現已82歲高齡的戈迪默依然心思敏銳,活力充沛。她是非洲黑暗大陸上一顆閃爍綻亮的良知之星,更是我們這個時代珍貴難尋的智性珪寶。她漫長的生涯,見證並活現了種族隔離制度從頑固走向崩潰的過程。儘管尼采(F. Nietzsche)曾經說過:「所有與歷史相類似的都是意外」。班雅明(W. Benjamin)也說過,:「『不屬於人性』的歷史無法為任何認知的主體所完全翻譯、意設或擁有」。但是,戈迪默以其藝術形式再現了南非一代人民為爭取尊嚴而鬥爭的歷史,在這之中,有著血光淚影一般的真實。正如法國哲學家雅克.馬利坦(Jacques Maritain)所言,「詩」來自一種靈魂深處的力量,詩人的職責就是承諾返回那個靠近靈魂中心地帶的隱蔽之處。納丁.戈迪默就是這樣一位詩人,她給讀者一種努力攀爬人類精神高原的熱力,帶領人們重回歷史「無私共享」的詩性之居。
作品閱讀:
1,葛蒂瑪,《朱利的子民》(July’s People)(內含《我兒子的故事》),莫雅平等譯,臺北:桂冠,1993
2,高迪默,《偶遇者》(The Pickup),梁永安譯,臺北:九歌,2002
3,高迪默,《我兒子的故事》(My Son’s Story),彭淮棟譯,臺北:九歌,1992
進階閱讀:
1,Ileana Sora Dimitriu, Art of Conscience: Re-reading Nadine
Gordimer,Hestia, 2000
2,Stephen Clingman, The Novels of Nadine Gordimer: History from the
Insid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2
3,Dominic Head, Nadine Gordim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4,Andrew Vogel Ettin, Betrayals of the Body Politic: The Literary
Commitments of Nadine Gordim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93
5,Kathrin Wanger, Rereading Nadine Gordim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6,Barbara Temple-Thurston, Nadine Gordimer Revisited, Twayne
Publishers, 1999
7,Brighton J. Uledi Kamanga, Cracks in the Wall: Nadine Gordimer's Fiction
and the Irony of Apartheid,
8,Judie Newman, Nadine Gordimer, Routledge, 1990
9,Rowland Smith, Critical Essays on Nadine Gordimer, Gale Group,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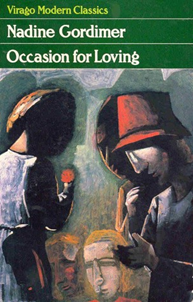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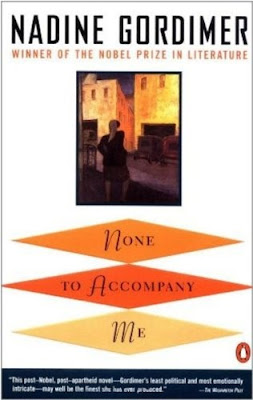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