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
George Orwell:1984
 |
| George Orwell |
一生從未擁有一部像樣的汽車和房子,寧願過著一貧如洗且極度厭惡英國上流社會的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本名艾裏克.布萊爾[Eric Blair]),是20世紀文壇上影響力至今未曾消退的重要作家。在繼《動物農莊》(Animal Farm, 1945)之後,奧威爾強忍末期肺結核的痛楚和絕望,仍以強烈的現實感和危機意識,寫出《1984》這部令人膽顫心寒的作品。通過生前最後一部作品,奧威爾建立了「政治寓言∕反烏托邦(敵托邦,Dystopia)的小說類型,為人類在20世紀中走過的戰爭和迫害,作出儘管是虛構但卻栩栩如生的體驗。
「反烏托邦」通常是指對一個「負面理想社會」(negative sane-society)的批判性描寫,但《1984》不僅是一部預示未來極權社會的寓言小說,它還涉及對人性黑暗面的深度挖掘和暴露。小說不僅通過「小人物∕大政治」的對比,展示了一種「全控制∕單意識」的未來世界,也展示了一幅級權統治下人類命運的灰色畫卷。
2+2=5?
小說描寫未來的1984年,世界只剩三個國家:大洋國(Oceania)、歐亞(Eurasia)和東亞(Eastasia)。三個國家都是極權主義國家,彼此仇視、不斷交戰。小說以大洋國為角度,該國首都設在倫敦,由一個從未露面但無所不在的「老大哥」(Big Brother)所統治。在這個「除了到處都是標語之外,一切都顯得黯然無色」的世界裏,「每一層樓口都有那樣一張大人像,眼睛釘在你的身上,隨著你轉,下面一行標語寫著『老大哥正在監視著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1]。人們日夜生活在電視螢幕(telescreen)和竊聽器的嚴密監控下,沒有思想言論的自由。「思想員警」(Thought Police)如蟑螂一般的四處密佈,他們天天破案,但罪名只有一個:「思想罪」(thought crime)。在嚴密的思想檢查和行動監視下,人們之間只有猜忌、徨恐和孤獨,個個成了溫馴聽話、無思想、無意識的空心人。
「大洋國」最高權力組織稱為「英社黨」(INGSOC),其權力核心稱為「內黨」,全由死忠的精英分子組成,這個統治集團信奉著三大口號: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大洋國」只有四個部門:「真理部」(The Ministry of Truth)、「仁愛部」(The
Ministry of Love)、「和平部」(The Ministry of Peace)和「富庶部」(Ministry
of Plenty);但實際上,真理部負責宣傳和說謊、仁愛部執行逼供和拷打、和平部規劃戰爭和迫害、富庶部製造苦役和貧窮。在這的極權世界中,只剩下一個人還在思考,這個人就是文士敦(Winston Smith)。他是一個尚未被徹底洗腦的人,他對「大洋國」充滿了怨恨和不滿,他與「文藝組」(fiction department)的裘利亞秘密相戀,這是他唯一能夠感受到人性滋味的事,儘管這帶有反抗意味的性歡愉總是短暫而機密的。在「大洋國」中,愛與性都是禁止的,因為除了對黨、老大哥以外,不能有其他的感情。實際上,文士敦與裘利亞的戀情從一開始就在歐布林(O'Brian)的秘密監控之中。文士敦起初十分欣賞並信任歐布林,把他視為同志和益友,但一切的友誼和關懷都出自於歐布林的精心設局。當文士敦所有「不忠」的記錄被蒐羅齊備之後,歐布林的真面目終於顯露出來。文士敦因無法承受歐布林的逼問、刑求和拷打,最後接受徹底的洗腦,向「黨─老大哥」獻出絕對的效忠:他從此相信2+2=5。
背叛與再背叛
《1984》的成功之處在於,它雖以虛構的方式但卻準確地預示了現代極權統治的技術與策略。在小說中,「老大哥」是一個陰魂不散的權力象徵,它所依賴的統治技術有二,一是監視器,一是語言。在「大洋國」中,電屏無所不在,它佈滿在行人道、樓梯口、走廊、高塔、街角、樹頂、草叢等等場所,它像一隻隻權力的眼睛,凝視並竊聽人們的活動和聲音,甚至連人的呼吸和心跳都可敏銳地捕捉到。然而監視本身並不直接產生統治,一如人們經常對著鏡頭扮鬼臉而無視於監視的敵意。一種「監視的政治」必須基於被監視者具有「反監視」和渴望自由的強烈欲望,並因擔心自由之喪失而對監視進行一種恐懼心理的自我再生產,監視才會產生統治的效力。文士敦最終走向崩潰而投降,除了身體的迫害之外,就是因為他無法承受恐懼心理的折磨,無法抵擋那種植入精神之巔和靈魂深處的「自我監視」,這就應驗了後來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謂「全景敞視監獄」(Panopticon)的理論,監視製造了被監視者習以為常、深化內心的規訓法則(discipline),人們依據這些規訓進行相互監視,甚至進行相互揭發和告密。實際上,再精密的監視器都不足為懼,但如果人人都接受了「監視者倫理」並產生彼此不信任的心理時,監視的政治就發揮了作用。
人們經常誤會自由屬於「公領域」的權利義務關係,實際上,自由的可貴及其真正實現的場所是在「私領域」,它表現在人們在精神密室中對公共規訓不經意的漠視或蓄意的背叛。文士敦和裘利亞的秘密戀情,意味著人們只有在私欲、私情與私密中才能獲得自由和安全感,雖然兩人的自由只能建立在短暫的肉體歡愉之上,但自由再少,依然可貴。
在公領域中如果沒有公平對等的社會程式,自由將只是一句口號;自由不在於程式或規則本身,而是在於「誰有權制定(或改變)規則」?在小說中,當權者建構了一種「全景監視」的社會,從表面的一言一行到深層的精神內室,都處於長期的、無孔不入的監視之中。但監視的權力並不掌握在監視者,而是「被監視」本身,也就是被監視者知道自己被監視,因而自動校正行為以符合監視者立下的準則或規範(自我監視);如果自由意味著私領域的背叛,那監視就是對這種背叛的「再背叛」,因為自由的最大敵人就是「被觀看」,因為作為精神私密的自由經不起長期的跟蹤或監看!既經不起正面的凝視或側面的旁觀,也經不起被審查和被記錄。自由只有在遮蔽、內藏、隱沒的空間中存在!但文士敦最後還是錯了,真正的自由還必須和勇氣相連結,逃避並不等於自由,但問題又來了,無論是積極的勇氣或消極的逃避都無法抵擋親人的背叛:文士敦之所以被殘酷地整肅,最早就是因為對歐布林的欣賞和信任,而文士敦最後被徹底擊敗,則是因為他夢中的話被自己的孩子偷聽到並向當局告密。自由如果沒有信任根本無法成立,但如果最值得信任的親人也會告密,這就使自由像似沙灘建塔、海市蜃樓。《1984》的重要啟示在於,自由何其脆弱,自由何其不堪一擊;「監視」表面上是為了確保忠誠和紀律,但實際上是為了背叛,特別是親人之間的相互背叛。
新話:靈魂改造工程
「老大哥」的另一個統治策略就是語言。文士敦所任職的真理部,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除舊佈新」,它一方面竄改歷史、消除人們共同的記憶,一方面收集「新話」(new speak)以偽造新的歷史,培養無思想的新人。它甚至用一種特殊的機器,把表現人類情感的故事和劇情進行絞拌,以製造新小說,目的就是要清除生活在過去記憶的「舊自由人」,製造絕對服從的「新奴隸」。
文士敦從事的就是這種塗改歷史、消滅記憶的工作,但矛盾的是,文士頓一方面進行湮滅歷史真相的工作,一方面又想在歷史材料中尋找反抗黨的依據。有一次他偶然獲得一張照片,這是一張黨代表大會上的集體合照,照片上有三個事後被判定賣國罪的同志。由於既是同志又是叛徒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照片本身也與黨的歷史相衝突。文士敦起初以為掌握了可以用來對抗黨的證據,但是他很快發覺,即使照片是關於過去事件的真實記錄,也已失去反抗黨的效力,因為照片中的人物雖然清晰可辨,但文字的記錄早已被多次竄改和變造,以致連真實的日期和事實都已模糊不清、真假難考。
消除人們過去共同記憶的最好方法就是創造「新話」取代「舊語」。大洋國的「新話」雖然還是從傳統英語的基礎上編彙產生的,但這種新話不再以傳達和溝通為目的,而是為了徹底清除人們運用語言進行反叛的思想能量,也就是「靈魂改造工程」。新話將所有的語言簡化為ABC三類詞彙,並且大量縮減詞語的數量和思想的範圍。因為語言的簡化就是思想的閹割,只要詞彙減少了,人們的思想能力就鈍化了,一旦思想退化了,人們就不會再有異端的言論,也不會再有「思想犯罪」的問題發生。最後,「無意識」就是正統意識,「無語言」就是絕對效忠,語言的極簡化就是極權主義最高境界的完成與實現。
《1984》最後的結局是悲慘和淒涼的,一切對自由的渴望皆化為灰燼,一切對人性溫暖的追求已成為泡影。所幸這樣的結局是虛構的。但奧威爾對未來世界絕望式的預想,依然具有「警世諍言」的作用,它教育了一整代世人要珍惜自由、警惕專制。指出人類生存最深刻的危機,不是為了危言聳聽,而是證明人類永遠不會停止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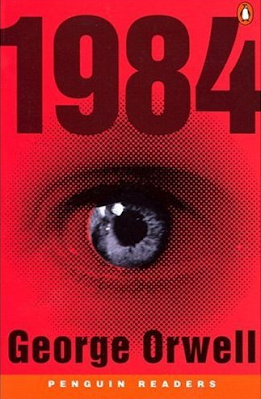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