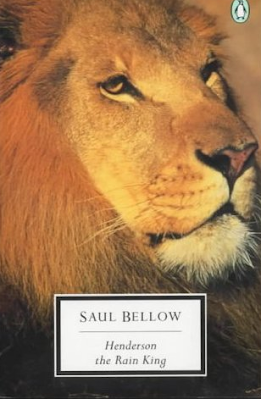42
梭爾.貝羅:《阿奇正傳》
Saul Bellow: 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
| Saul Bellow |
http://home.mokwon.ac.kr/~jtoong/bellow/pic02a.jpg
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運(A man’s character is his fate)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人生的價值在於尊嚴而不在於成功,這是1976年瑞典皇家學院頒發文學獎時對梭爾.貝羅(Saul Bellow)作品的贊詞。這一贊詞,就是指貝羅作品中的人物-脆弱但又勇敢、孤獨但不沉淪,一如《阿奇正傳》(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中那位終生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戰鬥的人。對於皇家學院的贊詞,貝羅顯得很謙虛,他只淡淡地說,富於感情的人往往顯得軟弱,總覺得自己全身充滿弱點,但假若他承認自己的弱點,承認自己的離群,並深入到自己的內心世界,不斷加深自己的孤獨感,他會發現,他和世上所有孤獨的人都是心心相印!
拒絕成為別人的兒子
《阿奇正傳》是一部融合現代寫實主義和古典神話寓言的自述體作品。描寫一位出生於芝加哥的猷太私生子的生活體驗與覺悟。小說一開始,說明瞭主人公阿奇(Augie
March)出生於那個景色暗淡的芝加哥,「對人處世完全依據自己學來的自由式(free-style),也用自己的方式寫下記錄」[1]。由於阿奇天性樂觀善良,這使他成為許多有錢人「收養」的對象。整部小說基本上就是在「收養」和「逃跑」中展開,一個在「拒絕成為別人兒子」和「追求自己生活方式」之間不斷拉钜和糾纏的故事。
作為一位猶太後裔作家,貝羅運用《聖經》中亞當被逐出伊甸園-流離人間-重返伊甸園三段式的神話結構,來描寫現代都市男孩從孤獨成長,經歷社會染缸,直到歸返平靜的生命體驗形式。實際上,《阿奇正傳》像似一部「折疊式」的敘事文本,貝羅在其中佈置了兩層世界,一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街角人物,一個反英雄的邊緣角色-阿奇,另一個則是希臘神話中的英雄象徵-被視為古羅馬英雄的埃涅阿斯(Aineías)逃離特洛伊重建羅馬城邦。貝羅並以聖經中的亞當作為兩個世界的串接人物,表現出一種從「淪亡-流浪-返鄉」之現代奧德賽的故事。在這個結構中,個人與社會被表述為一場關於真理本質的善惡鬥爭,在自我與外部世界之間,則被展示為關於人道主義與社會異化的永恆對抗。
通過阿奇這位猶太私生子,貝羅試圖表達一個具有自我個性的青年人對「社會訓導方式」的反抗。正如他的鄰居勞許祖母(Lauch),為了盡到把阿奇納入社會期待的軌道,為了把他教育成一名紳士(社會期許的男性形象),不惜教導他虛偽和說謊。在懵懂未知的少年時期,阿奇就被教導如何扭曲自己、壓抑本性以獲取社會生存的本領。在後來闖蕩江湖的日子裏,許多「善心人士」都想收養他,老闆娘考布林(Coblin)想收他作女婿,富商任寧(Renlin)夫婦想收養他做義子。實際上,阿奇並不是真正孤兒,只是一個父親自幼離家的「棄兒」,但每一次的誘惑和善意,都一次又一次向他證明自己「被遺棄者」的身份,向他表明社會孤兒的命運,而這正是現代猶太人的歷史際遇,一個被歷史所遺棄、任何人都妄想改變猶太人命運的寫照。阿奇拒絕了所有「成為他人兒子(女婿)」的命運,他要成為自己,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儘管他對自己的命運一無所知。阿奇雖然是這個「大寫社會」裏一個「小寫的我」,但他的心中始終藏在一的「大寫的問號」、「大寫的NO!」,努力抵抗他人的支配與期許。這種反叛性,正是一種「後猶太意識」-歷經創傷之後的自我奮鬥意識-在阿奇身上的反映,一種基於未知命運而對已知命運的拒絕與抵抗。
儘管阿奇對「自我生命形式」的追求一再破滅,為了生存,他不得不去從事各種投機和冒險,他給富翁作過秘書,幹過走私犯助手,當過偷書賊,甚至參與搶劫。在飽嘗辛酸痛楚之後,他仍然沒能成為他自己所期望的那種不被生活同化,不受別人控制的人,但他依然懷抱理想,始終追尋……。
資本主義-鳥獸社會
在貝羅筆下,無論是英雄還是反英雄,都是資本主義這個「異化社會」(alienated society)下的被壓迫者。貝羅塑造了一組人物,分別代表「疏離的異己者」和「認同的異己者」,兩者其實沒有差別,只是分別扮演英雄與反英雄的對立角色而已。如果阿奇是資本主義社會落難的小丑,那麼他的同胞哥哥賽門(Simon)則是個現代「異化英雄」的典型。賽門和阿奇一起渡過悲慘的童年,但長大以後卻走出完全不同的道路。賽門雖然完全認清資本主義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但他努力鑽營自己命運的縫隙和捷徑,努力學習富人的模樣和姿態,學習如何對女人諂媚、調情、求愛,一心想要攀登進入這個金錢堡壘的高峰。
與阿奇的失敗相反,「賽門很懂得政治手腕-知道怎樣向市政府的生意投標-他和選區裏吃黨飯的小角色見面,和員警親熱得像黨兄弟,他和巡官隊長之流交遊,也和律師、地產商來往,也和賭棍、外圍賭檔主,那些另有合法生意和產業的人混在一起」[2]。果然,賽門最後成了富人天堂的一員,但正如阿奇一再質疑的,這又怎樣?不過是個金錢奴僕,一個自己無法認清自己的、既「非人」又「非我」的「異化人」。
在小說中,最具資本主義異化特徵的就是婚姻,一種藉由婚姻或者攀龍附鳳,或者改變命運,或者另有圖謀所形成的買賣制度。貝羅把資本主義最可鄙之處表現在人們對婚姻的輕率、褻瀆、算計和虛假之上,而通常所謂的「成功者」就是善於利用婚姻作為工具的人。在阿奇年幼時,「祖母勞許」就灌輸他一種「鳥獸社會」理論,也就是把資本主義視為一個禿鷹競技場,在這個競技場內,奉行的弱肉強食的實力主義。他的老闆教導他,男人與女人只有肉體關係,男人與男人只有競爭與毀滅的關係。對阿其來說,這個社會教導他的不是溫暖和關愛,而是冷酷和無愛-無愛的婚姻、冷漠的鄰居、自私的同事、貪財的老闆。貝羅旨在突顯「工具性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優越性,這既是對美國主流哲學的嘲諷與批判,也是作為一個「後猶太作家」對自己的種族命運飽受政治強權操弄利用的深沉控訴。
「收養」(adaption)在小說中是一個重要的「認同隱喻」,它代表一整對資本主義金錢世界的皈依和順從。在阿奇眼中,收養是一種「階級信仰」,是有錢人一種「英雄慈善主義」的表現,「他們的信念就像羅馬的七座山丘那樣永恆不朽,只要把權威伸展出去,就能建立一座永恆之城(eternal city),然後等待那些不切實際的人把城市建立在沼澤之地以至土崩瓦解之後,來證明自己的真知灼見」[3]。對於像阿奇的這樣的孤兒,有富商願意收養,應該是有如喜獲上帝拯救一般,但阿奇拒絕了,為此,他再一次的逃離。正如埃涅阿斯背負老父、手攜幼子,逃離特洛伊重建羅馬城邦一樣。他要尋找自己的伊甸之園。
然而,命運往往既不是註定的也不是創造的,而是不確定的。當阿奇這種不願在別人的舞臺上扮演他人腳本的倔強,與冰冷的社會現實碰撞時,一種試圖去創造的命運總是回到原先註定的原點,重新給予一個新的未知,再度拋出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實際上,阿奇對自己既不抱熱望,也不對社會有所奢求,他既不在安適的現狀中久留,也不在未來的憧憬中迷失。他只是渴望一種「流動中的自我肯定」,也就是不隸屬、不皈依、不留戀,一種使自己永遠不屬於自身之外的確定性。
阿奇當然也有自己的理想,經過幾年的飄泊和流浪,特別是經歷了與西亞(Thea)-取自希臘女神之名-一場浪跡墨西哥的荒誕之愛後,他發現生命的意義有四個:真理、愛情、和平、慷慨。他希望和一個自己鍾愛的女子結婚,隱居在山林田野中,辦一所辜兒院,收容像他一樣的棄兒,然後再把他那雙目失明的母親、天生遲鈍的弟弟接到家裏,和自己的親人一起養蜜蜂、教孩子。這實際上不是什麼遠大的理想,而且最終也沒有實現。阿奇並不知道,自己活在一個連最簡單的理想都無法實現的社會,一個自己都無法做自己、無能為力的社會。阿奇最後不得不承認,命運之路的終點只是妥協和認命,或者是另一個不知去向的新命運的起點。
一切的生命來自母親的愛
儘管阿奇的夢想並沒有實現,但他依然感激。因為人活著,人能夠被生下來,都是來自「母親的愛」,而一切生命的欲望無不來自感激。在與米米(Mimi)爭論墮胎問題時,阿奇體會道:
我不認為所有的一切真是如此難受,幸福往往是人的幻覺,但人們依
然允許遺忘永久的失望,或永久的痛苦。儘管人們會遭受子女、愛人
、朋友的死,遭遇奮鬥的停止,衰老、口臭、死人的臉、白髮,乾癟
的乳房、脫落的牙齒,以及或許是最不能忍受的人的品格的墮落,像一
付老骨頭,有如第二付骷螻架子,在死前還在嘎嘎作響……[4]。
最後,阿奇體悟到,因為沒有安居之室,所以無法停止流浪,但他依然希望靜止下來尋找生命的軸線。他始終相信,也許最終無法達到,但只要不斷追求,世上的真理(the truth)-恩情、和諧、愛,就會像一堆禮物那樣,向你迎面送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