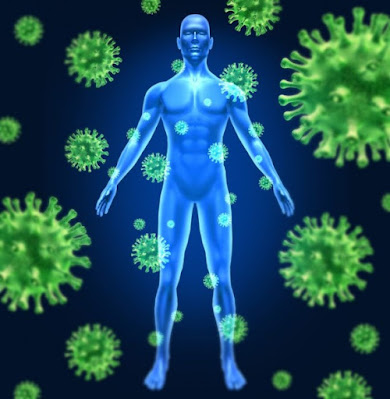回望20世紀
:20世紀的歷史學(1) William
McNeill(威廉・麥克尼爾)-2
在物種進化過程中,維持生態平衡最重要的環節就是「食物鏈」。所有的生物都是依賴另一種生物而存活,一種生物吃掉別的生物,但也被別的生物吃,人類也不例外。人雖然居於生態食物鏈的頂端,「但在「人科」動物緩緩演進至真正的人類時,周遭的各種生物必定也有時間來調整自己,以適應人類活動所帶來的風險與利益」(William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瘟疫與人》,楊玉齡譯,天下文化,2016,43)。換句話說,病毒侵入人體並在人體內尋找食物,在生態演化中一點都不稀奇,這只是一種「生態平衡」,是人類與其他物種共同演進中的「共享環節」。
除了大型生物(老虎、獅子)之外,侵犯人體的各種寄生物,種類多得驚人。「除了各種恙蟲、跳蚤、壁蟲、蒼蠅及蛔蟲之外,野生的猿類與猴類還是一大堆原蟲、真菌及細菌的宿主,更遑論還有一百五十幾種以上的所謂『節肢動物媒介病毒』(它們藉由昆蟲或其他節肢動物,由某個溫血宿主轉道另一個溫血宿主),也在這份名單上」(William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瘟疫與人》,35)。換言之,各種寄生物對人類的侵襲,是幾億年以來自然界極為普遍的現象,人類只是成千上萬個「宿主」之一。
只要人類與這種生態演化保持一致(在吃與被吃的食物鍊上保持均衡),即使做為寄生物種的長期宿主,人類的生存環境還是會保持一種自然的平衡。即使人類的基因產生突變(這是一種緩慢的過程),其他生物也會產生基因改變,以適應人類的改變並重新獲取平衡(在其他生物看來,人類也是一種可怕的傳染病)。這些侵犯人類的寄生物會始終並持續採取「互惠」的策略,與人類和平共存。
但是一旦人類改變或破壞這種平衡,互惠的策略就會失效,寄生物為了自己的生存,其對人類的侵害就或加劇或加速。例如,原先寄宿在蝙蝠身上的冠狀病毒,根本不會侵犯人體,因為人類住在高樓大廈,蝙蝠則住在深山的洞穴,各過各的日子。但是人類為了貪食野味或為了所謂(文化意義上的)「進補」,獵殺並吃了蝙蝠,冠狀病毒只有在人體內寄生以求取存活。McNeill說到:「當人類開始產生另一種演化,即把後天習得的行為,融入文化傳統以及符號含意的系統之後,原本存在久遠的生物平衡,開始受到新的干擾。文化演化開始把空前未有的壓力,施加在較古老的生物演化之上。新近襲得的技能,使得人類愈來愈有辦法已無法預料且影響深遠的方式,轉移大自然的平衡。因此,疾病侵犯人體的難易程度,也開始出現戲劇化的轉變」(William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瘟疫與人》,37)。
人類的大規模成長與擴張,得力於製衣取暖、生火熟食、築巢而居,以及大規模遷徙,並在其間增進獵捕能力並獲取大量新的食物。McNeill依據追蹤獵人的足跡,探索了人類進化的歷程。在人類從「樹居」跳到地上,進一步離開非洲雨林和熱帶草原時,人類開始進化到「智人」階段,「人類學會如何在天寒地凍的氣候下保持溫暖,例如生火及把動物皮毛披在身上,人類造成的影響又更可觀了」(William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瘟疫與人》,45)。McNeil說到:
「人類可以完成這項壯舉,是因為他們學會了如何替原產於熱帶的自己,營造出可以適應各種天候狀況的小環境。這套把戲就是發明各種衣物以及蓋房子,以便把人類的身體和外界極端的天后隔離開來,使人類即使在極寒的氣候下,依然可以存活」(William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瘟疫與人》,45)。
然而,另外一個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是,人類開始遠離疾病。「我們的老祖宗在遠離熱帶環境之後,同時也拋開了許多寄生蟲和病原生物,這些病原生物原本都是它們的祖先以及留在熱帶的同伴非常熟悉的。於是,遷移之後的族群健康和活力大增,終於使族群人口增加到史無前例的規模」(William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瘟疫與人》,45-46)。
然而,人類的進步,特別是人口的增加與聚集,卻也給病毒絕佳的生存機會;他人可以快速而輕鬆地在人類宿主之間轉換和傳播。一如古代人類在大草原上可以獵殺源源不斷、取之不竭的野生動物一樣,病毒只要依賴人類密集的接觸(僅僅是咳嗽或聚食),就可以輕鬆自在的轉移宿主(也就是大規模快速的傳染)。McNeill說道:
「食物生產技術使得人口數目快速攀升,而且很快的促成都市與文明的興起。人類族群一旦集中在這樣大的社群中,等於是對潛在的病源生物,提供了異常豐盛且唾手可得的糧食,這種情況就彷彿非洲草原上的大型獵物,曾提供豐盛食物給我們的遠祖一樣」(William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瘟疫與人》,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