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親朋無字病孤舟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
 |
| 聶華苓 |
《桑青與桃紅》是旅美臺灣作家聶華苓的代表作,被視為中國現代離散書寫和流亡自傳的代表作。作品跨越1945年至1979年,經歷了抗戰、大陸淪陷、來台與赴美,通過一個「離散∕分裂」女子—「桑青∕桃紅」一生的飄泊與創傷,表達了一個中國人終生的流放與疏離,透視了一個紛亂時代下個體生命的殘缺與破碎。
離家、離家、再離家……
小說的總體架構是立體的,也是多層面的。就立體而言,它展開於歷史和個體之間互為糾纏的兩個世界:歷史表現為巨大的荒謬與狂亂,個人則表現為無力和軟弱,這其中,存在著巨大的乖離和擠壓;就多層面而言,小說分裂為現實與寓言兩個空間:現實表現為頑強的殘酷與無情,寓言則呈現分裂的幻覺與虛無。
時代變局和個人的流離,無止盡的逃亡、奔跑、躲避、分裂和崩潰,乃至最終全部存在意義的喪失,構成了小說的主題。小說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描寫桑青離家出走,遠赴重慶的曲折經歷。小說主人公桑青以一個年僅16歲的懵懂少女出場,當時正值抗戰後期,煙硝與戰火襲捲整個中國。然而桑青的離家並不是出自愛國熱血,也不是救亡圖存,而是極微小的個人因素:不滿母親對弟弟的溺愛以及令人窒息的封建家庭。桑青與女同伴老史一同計劃前往大後方—重慶,一個凝聚民族意志的「抗戰中心」。她們嚮往「愛幹什麼就幹什麼」的豪情壯志,夢想住進「流亡學生招待所」,一解那久經壓抑的青春心志。然而命運多蹇,時代弄人,在她們還沒來到重慶之前,日本已經投降。一場青春之夢擱淺在瞿塘峽的惡水裡,一顆渴望闖蕩江湖的野心跌落在崎嶇的彎路上,未知的命運灑落在逆流而上的破木船之上。
逆行、逆行、再逆行……
木船逆流而上,途經黃龍灘、鬼門關、百牢關等眾多急流險灘,象徵著民族處境的艱難和命途的多蹇。破木船、擱淺、急流、巨石,意味著杆格、險惡、危機和恐慌。小船在江上整整困了七天,飲水和食物都已用盡,絕望就像那江邊石壁上茂密如雲的巨木,遮蔽了希望的陽光。船上擠滿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流亡學生、老先生、桃花女和她的小孩、船老大;這艘小船,實際上是民族苦難的拼湊與集合,是中國人民多樣性格的濃縮,更是中國人原始生命力的表徵。
突圍、突圍、再突圍
小說的第二部分描寫桑青來到了北平,此時中共解放軍正大軍壓境,圍逼北京城。桑青奉父母之命和封建舊規,與一位富家少爺沈家綱結婚成親。沈家是一個舊式大家庭,但豪門之內陰風慘慘,散發著腐朽、垂死的頹敗氣息。
在這裡,聶華苓給「圍城—出逃」的景象一種振鼓擊歌式的描寫,在歷史、空間、古城、個體之間,再度撕裂、瓦解、剝離。家如空樓,人如螻蟻,新軍奏歌、敗兵潰逃。儘管舊體制的崩解令人喝采,但新中國的藍圖誰來塗寫?聶華苓用她實驗性的象徵語言,給這個時代一種哀怨式的吶喊;倉惶中的茫然,回眼中的低泣,如此怦然!驚慄!燥動……。在這日落的北京城,在黃煙滾滾的逃亡路上,一波接一波、一浪逐一浪的難民潮,空氣中充滿著恐懼與不安,人影中抖落著不捨與茫然。這又是一次的困,又是一次的逃!桑青不知,這「困與逃」的命運之謎如何解開?這渡海遠離的旅程,將歸向何處?
奔走、奔走、再奔走……
第三部分描寫桑青夫婦逃到台灣,定居在臺北一條小巷中。桑青的丈夫因為挪用公款,遭到臺灣警方通緝,全家人藏匿在一個昏暗小閣樓裡,度過了兩年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的生活。這間小隔樓,搖搖欲墜、塵埃滿布、白壁脫剝、老鼠橫行。危梯、搖樑、腐木、爬鼠、塵灰……,這一連串破落的空間意象,既是「白色恐怖」年代的縮影,又是異鄉人的避難窩,令人失神、苦悶、癱瘓。在這裡,「閣樓」,又是一種「困」的意象,又是一次恐懼與不安的凝結,又是一次白日與黑夜的交纏,以及那揮之不去的孤絕、封閉和呆滯。
對於當時台灣這個特務四伏、警監橫行的恐怖年代,聶華苓以「超現實—荒誕」的手法,給予一種陰森而淒苦的描寫。桑青一家三口終日擠在這間小閣樓裡,為了怕外面的警察查覺,也憂心小女兒桑娃受到驚嚇,她們不敢正常交談,更無法享受天倫之樂。但是內心的恐懼需要傾吐,於是她們用「掌心語」—把字寫在手心上—來互通情感,互相安慰。
「掌心語」是一種恐怖的語言,但它既傳神又貼心。在這種「觸感傳心」的交流中,時間雖然被凍結,空間雖然被封閉,但就在那手心的溫熱傳導中,至少感到心還能跳動,血還能行走。但桑青並不知,自己已陷入精神分裂:在日記裡,桑青把自己寫成了一個「吃人的人」……。
為了排解抑郁和沉悶,桑青用「剪報」來揣探外界的變化,這實際上既是作者以「後現代拼貼」的手法,對當時國民黨的獨裁政治進行影射與批判,也是身落異鄉一種破碎、孤立、零亂的心境表達。剪報中貼滿了各種光怪離奇的事件:僵屍吃人、荒山黃金夢、三峰真傳固精術、分屍案…..。在這裡,作者展示了一個分裂的二重世界:現實世界不能真實體驗,因為一旦被捕,那將是永無天日的牢獄和監禁,小女兒因為長期孤立以致不能直立行走,但幻覺世界裡的一切記憶卻歷歷如生,它像從夢中跳出的厲鬼,像白日行走的幽靈。
逃離、逃離、再逃離……
丈夫終於被捕,於是桑青逃往美國,小說進入了第四部分。這又是一次掙脫之後的逃亡,但也是逃往另一個更難掙脫的困局。此時的桑青已成為一個精神分裂、縱欲狂歡、無家可歸的浪女。面對美國移民官,桑青失去了自我辨視和自我定位的能力。移民官給她一個名字:Helen .沈,這種中文為姓、洋文為名的拼貼,不是融合,而是徹底的斷裂;「沈」是一個甩不開、剪不斷的根,是原鄉認同的濃縮和標計,Helen是一個借來的異國符號,沒有選擇,也毫無意義。這種組合,正是那一代離散中國人「失根」的象徵,一個無依可皈的破碎身份。
在面對美國移民官員的詢問時,她否定了「桑青」,同時也否定了一個真實存在的過往,他說:「我不是桑青,桑青死了」。一句桑青死了,既是精神崩潰的自我否定,也是心體分裂的自我肯定。無論是崩潰還是分裂,它說明現實已無法承受,時光無法倒轉,生活無法回味;一種自我幻覺,一種精神自殺之後的自我茫然,成為唯一的解放,唯一的出路。
桑青否定的是什麼?一個真實的自我,一個生在中國文化悲劇和歷史滄桑中的自我,一個具有文化主體和身份辨視的、但卻是沉重得無法承擔、無法背負的自我。但是,桃紅是新的自我與人生嗎?也不是,它只是一個假名、一個替代、一種掩護,即使這個名字聽起來光豔鮮麗,富有青春與希望,但卻是一個在公路上盲目奔逃的幽靈,一個無法死而復生的軀體。於是桑青既已死去,桃紅也活不過來。最後,為了躲避移民局的追捕,他只能在異國權力的查緝中,逃跑、逃跑、再逃跑……。
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是中國現代流亡文學的佳作。儘管作者自謙只是一部浪子的悲歌,但作品橫跨中國、臺灣與美國,歷經抗戰、兩岸分離、台灣威權時代以至流亡美國,既是一部國族悲劇的歷史史詩,也是個人飄泊流離的血淚記錄。作者幾乎調集了所有現代小說的語言技巧和創作實驗,從時代變局到個人內心,為那曾經飄浮和失根的一代,寫下了一部藝術珍品,留下了難滅的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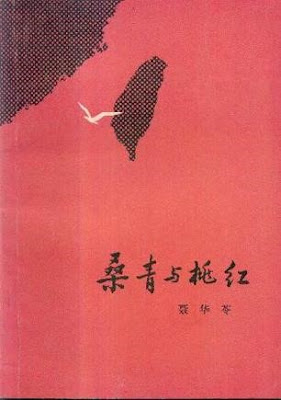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